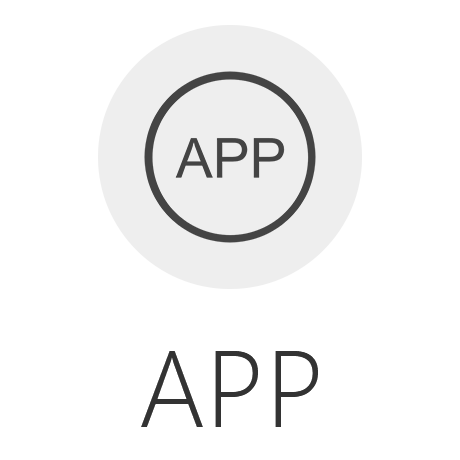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大会发言(图片来源:大菩文化 摄影:妙雨)
大菩文化福建讯 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在福建省莆田市召开。论坛主题为“交流互鉴、中道圆融”,邀请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学者等约800余位代表出席。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出席大会并发言。以下为讲话全文:
佛教与中国文化
历史上东方两大文明,即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借助于“一带一路”,终于在两汉之际实现了对接,作为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所指出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那么,印度佛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土生根、开花?它又结出了什么样果实?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佛教自身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的重要问题。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土立足,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走的是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就学理层面说,佛教中国化的特点,就是在坚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大量地吸收儒家、道家的思想,把外来的佛教变成了一种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相因应的中国化的佛教,其典型代表就是禅宗。
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特别是慧能南宗)已经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向中国化佛教的华丽转身,此中最关键的节点,是“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心即佛”的佛性理论;二是“道由心悟”的修养论;三是“即世间求解脱”的解脱论。三者背后都有儒学的身影---概而言之,慧能南宗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坚持作为佛陀本怀的基础上,吸收融汇了大量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种吸收融汇几乎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以致人们现在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思想是源于印度,哪些思想是出自中土。实际上,这种融合是一种契理契机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但使中国佛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如何融汇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更多地表现为双向的交流互鉴,在相互融摄的基础上,发展自己,成就对方。例如,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另一方面,那些中国化了佛教又反过来对中国本土的学术文化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此中尤以佛学对于儒家哲学、道教思想以及诗书画等文化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和深刻。
以宋明理学为例,宋明理学又称“新儒学”。而“宋明新儒学”之“新”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先哲时贤对此曾经有一个评论,曰:“儒表佛里”、“阳儒阴释”;而朱熹在评论陆学时,曾指责他“全是禅学”。
这里所说的“儒表佛里”、“阳儒阴释”。指的是宋明新儒学所讨论的大多是儒家的话题,如人伦道德、修齐治平等等。但宋明新儒学借以依托的思维模式,则是隋唐佛学所建构的心性本体的思维模式。
再看看佛教对于道教的影响。传统道教“贵生重命”、“仙化为上”,受佛教“中观”思维模式的影响,到了隋唐的“重玄学派”如成玄英、王玄览等,则大谈“双遣二边”、“境智两忘”、“非有非无,而有而无”,与中观学之“离四句,绝百非”如出一辙。
北宋之后的“全真道”。在吸收融摄佛教的义理和修行方法方面走得更远。“全真道”一反传统道教的注重符箓斋醮、仙草丹药,而强调反省心性、闭炼内修,甚而把禅宗直探心源、强调明心见性作为“达本明性之道”的“最上法门”。
而向来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冠冕之诗、书、画,受禅之影响,更是广泛且深刻,例如,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南北朝山水诗,清代诗人沈曾植曾有评论,曰:“康乐总山水老庄之大成,而开其先者支道林。”此中之支道林和康乐公都是佛门中人。
唐诗之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都深受禅之影响:
李白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
杜甫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
白居易早年不信佛、道,但自江州之贬后,深知仕途艰险,于是寄情于山水诗酒,借旷达乐天以自遣,转而炼丹服食,崇信道教,继而皈依佛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号香山居士。
另一个受禅宗思想影响更具代表性的唐代诗人是王维。
王维号“摩诘”,其诗文的内容多是空山日色、青松翠竹、鸟啼花笑、流水钟声,但所表现的多是一种圆满自在、空灵和谐的真如境界。这类诗的特点,是不以文字、议论、才学爲诗,而是以“但睹性情,不立文字”爲宗旨,既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又平淡自然,深入人心,如花落香浮,月印水底,非有妙悟,难以领略。正如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这类诗的最大特点,是“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是当行,乃为本色”。
对于诗与禅的关系,元好问有一句点睛之笔,曰:“诗爲禅客添花锦,禅爲诗家切玉刀”。亦即禅的注重顿悟的思维方法,乃是诗之工具和灵魂。
中国历史上的书画,更与禅有着不解之缘。从书圣王羲之,到狂草怀素,再到苏东坡、黄山谷,都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书法与佛教之修行方法,如戒定慧三学,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如“戒”重在“收束身心”,“定”旨在“专志凝神”,“智”则“穷巧极妙”,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
蔡邕说:“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王羲之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字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画家及中国画与禅的关系,沈灏在《画尘》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阐述,他说:“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南则王摩诘,爲文人开山,荆浩、关仝、巨然、、董其昌等,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赵干、马远、戴文进、吴小仙等,日就狐禅,衣钵尘土。”
有些画论家在评论宋代的绘画时也说:“宋代佛教对绘画之另一贡献,则禅的心物合一境界与禅的空灵境界,使画家不仅知写实、传神,且知妙悟,即所谓'超以象外'。”“论画者,喜言唐画尚法,宋画尚理。所谓理者,应爲禅家之理,亦即画家所谓气韵。”
总之,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成人达己”的关系,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相互交融互摄过程中,既发展了自己,又成就了对方。而那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佛教,就很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